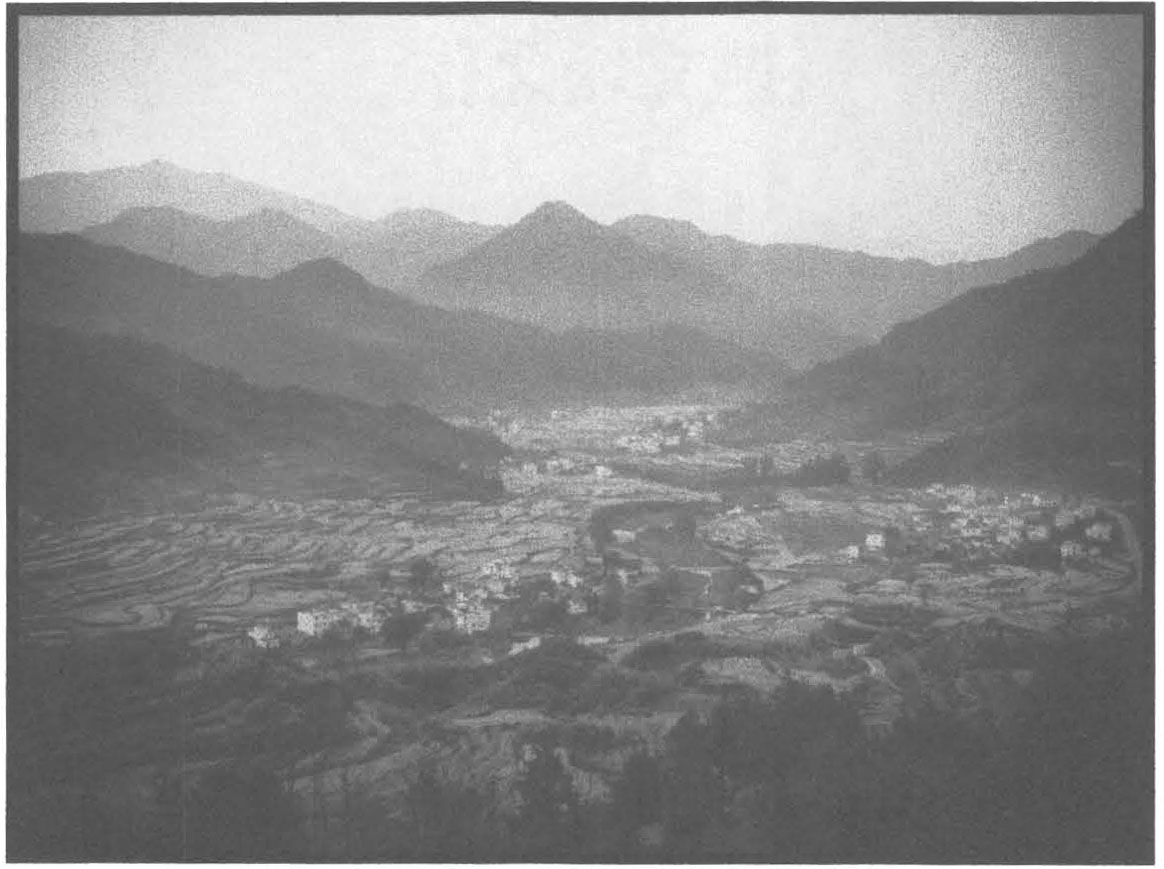释果淳
因缘
是因缘使我认识了林清玄先生。第一次,在七十二年(公元一九八三年)金鼎奖颁奖盛会中,从远处望见他,高举着奖杯,似洋溢着满心的欢喜,而惹人注意的是他那属于艺术家格调的好长的头发。
时隔一年多,为了编辑《人生》,经常往返打字行。无意中瞥见淡大同学的一则访问稿,主角恰是林清玄先生。他素食,喜读佛经,而言谈中自然流露出来的见解思想,也开朗明阔地一如佛法。
几天后,《中国时报》副刊登出了他的近作《佛鼓》,文字上多着墨于佛寺的钟鼓雍穆,殿堂圣洁,涵意中却又点化出了佛法深隽自得的心地功夫;理会得到,林清玄先生,绝非是以佛学珠串来华饰他文学殿堂的域外人,在他灵敏的文思所倾注而出的光彩内,已显露了一个慕道者对佛法全心的喟叹和挚诚的期盼。
最后,由一份单张的书讯报导,得知了作家林清玄先生全家茹素的消息,并据称素食有益身心健康。这一讯息,使我欲代广大读者和林先生结缘的念头,愈益成熟,于是,托请在杂志社工作的三姐,探得林先生此时正于《时报杂志》担任主笔,几番电话联络上了之后,听筒中传来的声音,十分爽亮悦耳。巧的是,林清玄最近也读了《人生》杂志,并正计划和太太造访农禅寺。此一邀约,竟是这般顺利;首先,林清玄和夫人在七月初相偕来到农禅寺,由于当时事务正忙,招待不免简慢;而《人生》编辑组,也趁着林清玄工作较轻闲之际,至其家中,相与畅谈,前后历时四小时,透过他丰富的触感,条理的思维以及妥帖完整的铺叙,我们逐渐了解到文学和佛法,作家与佛教徒这一脉相承,婉转而来的心路旅程。
神奇的民间信仰
童年,我生长在一个宗教信仰气氛极为浓厚的家庭里,父亲以上三代,对寺庙事务都非常热衷。父亲本身是一家“如来佛祖坛”管理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而旗山镇妈祖庙的土地是他捐献的。每逢庙会、游行,他总是掌头旗,做炉主;旗山镇大大小小的寺庙,大凡柱子、供桌都刻有父亲的名字。从小,我便经常随着父亲四处去参拜。
我们家有个房间,摆着一张很大的供桌,上面供奉着许多神像,早晚都必须点香。大年初一起床以后,全家第一件事,就是环游着全镇的寺庙一一去上香礼拜。寺庙,对我们以及全镇的居民而言,简直是血浓于水的关系。每天,下田工作前,父亲会先去庙前的广场喝几盅老人茶,下午,收工以后,也是先喝了茶再回家。凡是遇到妈祖生日、观音生日,盛大的集会、游行,那更是全镇的人都一齐丢下工作,集合起来,全心全意地投入一场宗教式的喧腾中。
是什么力量驱使他们,如此为宗教活动忘情忘身地参与?我想有两点,一来是基于崇敬祖先的心理,因为寺庙所供奉的神明,大部分都是我们的民族伟人。二来那些层出不穷的神奇现象,确实带给了民众强烈的鼓舞力量。
我小时候,曾亲眼看到,神轿由人抬着,从一条大河上面漂浮着踩过去,而这条河在平时,足足可以把人没到头顶。还有神明出巡的时候,沿途都会收罗天兵天将,乩童一跳,挥刀向四边的草木砍杀,那些植物竟然会受伤流血。有一次,乩童口中忽然讲出日本话,原来收了一个日本兵,连他的兵籍号码都报告得一清二楚,年纪大的人劝他说:“你来这里做中国兵,应该讲中国话!”于是,他立刻改口讲闽南语。这些例子,不胜枚举。还有过火,一次几千人参加,每一个人都平安通过,我有一篇文章就叙述小时候过火的体验。
更有一桩了不得的奇迹,是轰动我们整个旗山镇的,我可以详细说明一下。
在旗山镇,有一间小庙,供奉着地藏王菩萨。他每年农历四月总要回安徽九华山谒祖。一九八二年四月十四日的晚上,这座寺庙的管理员、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都同时得到菩萨的梦兆,指示众弟子在四月二十一日卯时,前往台北县石门乡富贵角接驾,届时将有佛祖释迦牟尼同来。大伙半信半疑地依时循地前往。时辰一到,海面上果真漂来一块黑黑的木头,浪头打来,便跳上了岸,是一尊释迦牟尼佛,佛像背面刻有“苏州府归宁寺”字样。而乩童跳乱时,地藏王菩萨又表示,他一共迎请了归宁寺三尊佛像。第二尊要来的是“药师如来佛”,抵达时间是农历五月三日子时,地点在台南县七股乡海边。
这下信徒可疯狂了,谁也不敢不相信,浩大的车队,准时前往等候,但海岸线太长了,晚上海边能见度又低,苦候了一夜,没见到佛像的踪迹。原来,这尊药师如来佛,被一位货车司机在海边捡到,便移至“镇海将军官”供奉起来,信徒沿着海岸询问数天之后,终于找着它,完璧归赵。第三尊是阿弥陀佛,将于八月十日酉时在狮头山海面登岸。那天海面风浪很大,可是,佛像却自海上缓缓漂来,安详而宁静。
现在,这三尊佛像并排着供奉在地藏王菩萨庙里,用上好的乌沉香木料刻成,高约二尺,据说是明朝以前已雕成。
这怎么解释?从苏州过来台湾,翻山越岭,漂洋过海,有几千里的路程,竟都能够准确地抵达目的地。除了神明的神力之外,还能有其他更好的解释吗?
对于这些司空见惯的神迹,不止是老一辈的人置信不疑,我们这批已经接受新式教育的年轻人,也不免咋舌,每年选举新炉主的时候,按照惯例,都是以笠杯决定,当有人连续掷出正反正反三十多次,大家都想今年炉主非他莫属,结果竟有人出现了六十多次,全部的人都鼓掌叫好,而最高纪录可达八十多次。用现代数学的概率来计算,根本不可能,那是几亿分之一的机会,但这种现象,在乡下很平常。
然而,在这些言之凿凿的神迹及浓烈的宗教气氛之外,我也开始有了些反省。我想知道,这些神明他们除了显现神通之外,平常他们在做些什么?如果他们真能造福人类,这世界为什么仍然充满了缺陷及痛苦?那些乩童为什么老是要用尖针刺穿嘴巴,用利刃砍伤背脊,受这些无谓的折磨呢?庙会游行的时候,为什么要把小孩绑在旗杆上,都尿在裤子上了,也不放他下来。这样的信仰是不是最好的?
对乡下人而言,这样的信仰方式已经心满意足了。他们不需要去知道太多的理论或依附一个中心思想;也不去问人生的意义何在或人死后到哪里去,这类更深一层的问题。反正有神在就好,它是神圣的表征,高高在上的主宰者,人间发生了大大小小不可化解的疑难杂症,一并交给神来决断。重要如婚姻、事业、健康,鸡毛蒜皮如家里走失了一条狗等,都得请神来指示,而且时常都很灵,万一不灵,乡下人也能够包容并且认命。
在旗山镇,由于这种民间信仰非常神奇而强烈,所以,基督教、天主教一向被排拒在外,但正统的佛教也无法占有一席之地,这可能跟乡下人爱热闹的性格有关,佛教仪式通常都清净庄严,而佛菩萨也很少有特别突出明确的示现。
虽然,佛教并不否定神迹,甚至经典里面描述了许多大菩萨们的神通境界,然而佛教的特色却强调觉悟,能于生活中觉悟到清净的智慧,才是重要的。
我有一次为了写报道文学,曾跟着大甲妈祖回娘家,从大甲走到北港,需要七天七夜的时间,这么虔诚盛大的队伍,无论走到哪里,沿途都有人替你弄吃的,找睡的,而这么多人,并没有特别的管理约束,多少年来,不曾听说过有冲突事件发生。到了北港朝天宫,几万人聚集在广场前,一齐拜下,那种场面实在令人感动。我觉得佛法若要弘扬,佛教徒应该对此抱着宽容的态度,了解了民间信仰力量的来源之后,才能实际替他们开辟一条新的出路。星云法师说过,迷信没有关系,就怕没有信仰,乡下人全部的精神寄托,就在这些迷信上,至少他们的宗教需要,在这样的信仰模式中,已经得到暂时的满足了。
我的文学里程
而我自己,对于宗教信仰,一直保持着若干兴趣,只是,还不到想要依靠的程度。出外念书时,也接触过基督教,跟着做团契,觉得基督教的性格太狭隘而激烈。天主教比较宽容温和,但圣经上又留给我太多的疑问,令我觉得不够圆满。佛经我也涉猎过,心经、金刚经、六祖坛经、维摩诘经等,当时,我是把它当作哲学性的书籍来阅读思考,不知道以那种方式去理解佛经,完全是错误的。而我主要的生活重心,还是从事文学创作。
其实,小时候,我更喜欢画画,稍长,觉得文字才是最直接、最有力量的表达工具。比如写情书,与朋友问候沟通,都不能不运用文字。我的个性又比较敏感、好奇、喜欢做深入观察,我愿意去挖掘、表达我所接受的讯息和感受到的心得,来促进人跟人之间进一步的沟通。
高中时,我第一次投稿,稿酬三百元,正好是一个月的食宿费。从那时起,我更积极地写文章,久而久之,写作就成为我谋生的技能。
一旦决定要当一个作家,我便考虑作家的条件,必须是写得比别人好,比别人快,比别人多,我要如何达到这些要求呢?最初,我规定自己每天写一千字,一段时间之后,增加到每天一千五百字,若写不到这数量,就不睡觉,等于固定的功课。而一共有十年的时间,我维持每天写三千字的习惯。
我把作家当成工作,和一般农人、工人没两样。农夫种稻,自播种到收成,得经过四个月的时间,并且每天都要下田悉心照顾。作家写作,也像每天在耕耘一样,但却不知何时才能创造出最美好的东西,而态度上必须是不断地耕耘,不期待收获。
在不断写的过程中,我也一直寻求突破。我的方式比较特别,就是改变生活,出去旅行,更换工作。比如我去梨山采梨,在一两个月当中,便可以完全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性、工作甘苦、娱乐范围等。我也随着矿工一起下矿到三千米处去挖煤矿,这时所有的人都挤着要告诉我做矿工的条件。我写作和待人的态度是相同的,也就是你必须和你相交的对象站在同一基础上来看事情,如实地了解体验之后,才能生出真诚的同情。而任何一篇好的作品中,这份真诚的素质,都是不可或缺的。
但有人写文章却提出了“文学的价值,在于形式,而不在于内容”的口号。形式指的是技巧,用技巧来作为内容的衬托,当然是重要的,但我觉得不该把它摆在第一位,否则,就变成雕虫小技,失去作家的意义。
要比技巧,书架上随便抽出一本文学名著,技巧都比我们高明,但为什么我们仍然要写?正因为我们跟他在不同的时间、地点、身份,有不同的感受和需要。一个作家的独特性,应是从这些真实的情境中来发挥的。
比如,我曾听一位茶农,叙述在茶叶收成季节“忙”的情形。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有一天采茶回来,便坐下来炒茶叶。添了一碗饭,才扒了一口就睡着了。结果,饭碗跌碎在地上,而他人就趴在饭粒当中睡觉。然后,做了一个梦,梦到自己的茶叶炒焦了,突然惊醒,才发现口里仍含着一口饭,并且已经散出了酒味。你看,他形容这“忙”,形容得多好,只要将这事实描写出来就够精彩了。而生活中,这样的题材到处可见,只要我们细心观察,便有所得。
谈到题材,又关系到作家的良心和责任问题。有人说作家要讲纯粹性,这是值得商榷的。我想没有一件东西是纯粹的,作家写完一篇文章,放在抽屉里,这叫纯粹,只要拿出来,譬如拿给我太太读,这已经不纯粹了,因为我会影响她。更何况将它公之于广大的读者面前呢!所以,作家写作,一定要考虑对象问题,不能逃避社会,若因自己的邪见、堕落、淫秽,而影响别人,这罪过就太大了。像我的读者中,有小学六年级的,有初中生,他们不见得有足够成熟的看法和见解来判断是非。堕落与罪恶是古今每一个社会共通有的现象,而作家也不是不能写堕落,像旧俄的小说,有许多堕落的场面,但他写堕落,是为了救赎,最后的目的,是要激发更大的拯救力量。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能力,或根本没有这种动机,我想还是不写的好。
除了增加生活阅历,我也用其他方法来加强写作能力。例如:我曾固定以三百字为限,来写任何题目,训练自己把不必要的枝节删除,留下最精华的部分。我也将写好的文章,拿给年纪大的人看,或让三年级的小朋友欣赏;如果他们说太难了看不懂,我就把它改成最平淡的方式。
另外,如果想扩充写作的素材,观察力和联想力相当重要。小时候,乡下牧场里养许多牛羊鸡鸭,义卖水果,要做很多琐碎事情,一旦忘记了,就会挨揍,因此,养成了我对生活观察记录的习惯。比如,我当兵时注意到训练伞兵的塔台正好是三十四英尺(约10.36米),为什么不是更高或更低?便去问教练,他们说这是规定,没有理由。但我不服气,继续追问,终于有一个教练回答了我,他说据心理学家研究三十四英尺是人类最恐惧的高度,你从三十四英尺跳下来会死亡,但并没让你有解脱豪迈的感觉,反而觉得很窝囊。如果低于三十四英尺,那你不会死。因此,一个伞兵,如果能通过三十四英尺的考验,那更高或更低的高度,就都不怕了。像这样,大家都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你观察到了,自然会有不同寻常的领会。
我的菩提路
我的文学里程,可以说相当顺利,谁也没料到,最后我却走入了佛教。
在信佛之前,我的性格也比较随便,除了初高中时,年轻气盛,凡事爱和人争个对错是非;而近十年来,我没有再发过脾气。
我的原则是,你要我就给你,我自有天地。
我曾见过一种斗鱼,水蓝色的,非常漂亮,只要两只鱼摆在一起,非斗个你死我伤不罢休。后来,从书本的研究,我了解到,原来,这种斗鱼天生有爱划地盘的习性,困难就在,它所划定的地盘通常要比鱼缸大,为了不让别的斗鱼侵犯领土,只有抵死拼斗了。
这种斗鱼,如果它有一个广大的海,那根本就不成其为斗鱼。因为海的广大,使它能够随时建立新的地盘,所以,我们若是在海里面看到斗鱼,反而会觉得它非常的美丽又温和哩!
人也是一样,一旦划定了一个狭窄的势力范围,那非跟人相斗不可。不论是物质的或心灵的,我们一旦执著起某一个特定的据点,便会没有了自己。根据斗鱼的启示,我就写了一篇文章,说明如果人人都来试着开辟自己更广阔的天地,便能减少争斗,使生活变得更自在、丰富起来。
这是我学佛之前的观念。而我的朋友就问我:“你写作顺利,工作顺利,太太孩子都好,身体又健康,怎么突然间信起佛了?”确实,在生活上,我并没有遇到什么难题,我遇到的困难都只是内心的关卡,那就是如何突破我生活的层次,文章的意境。
最初写作,我也总是围绕着自己的朋友、爱情等零碎的琐事上大做文章。一段时间之后,我写不下去了,你一直告诉读者你自己、家人以及你的朋友在干吗等等,这有什么意义呢?后来,我开始写报导文学,有几年的时间,我一边旅行,一边写作,希望借着对某些事件的回顾探寻,以引起社会大众普遍的关心及帮助,但这也没有收到多大的效果;于是,我改写有关台湾或中国文化走向等思考性的问题。总共我所写过的题材包括,小说、散文、诗、剧本、报导文学、评论等,而直到信佛以后,有两三个月的时间,我没写过任何文章,除了佛法以外,我似乎已无话可说。
我正式成为佛教徒,是今年过年前后的事,那段时间,我突然厌弃了当时的生活形式,就是喝酒、应酬、打麻将。因为从事新闻工作,无非要借着这些活动,来维系人际关系。但有一次,坐在麻将桌前,看见麻将哗啦啦一阵翻倒,不禁警觉自问:“我坐在这里干吗!为什么会这么无聊地重复这些动作?”为了替生活谋求一个更安宁的境界,首先,便把麻将戒绝了。
刚好,我太太也同时厌倦了这般忙乱无绪的生活形式,她开始吃不下鱼虾,足不出户地静静地看起佛经,而我们又遇见了好几位以前的朋友,有的是从美国刚回来,他们竟然都信佛。由于我对佛经还有一些知识层面的了解,大伙便谈佛论道一番。朋友随即对我说:“你既然很有兴趣,就该做一个佛教徒!”
之前,我心目中佛教得是成天吃素、戒酒、礼拜、诵经等,一些很公式化的印象。我时常嘲笑别人吃素没出息,而我的酒量又公认地是千杯不醉,戒酒,绝对办不到的,至于趴在地上,向佛像礼拜,总觉得有损知识分子的尊严,况且,一部经念一遍,懂它的道理即可,为什么佛教徒却要对着同一部经每天不断地诵它,这有什么意思呢?
但此刻,我却感到也许尝试去做一个佛教徒,正是我脱离目下这种生活形式的大好机会。
过年的时候,我和太太一起回旗山老家,满桌大鱼大肉,她却只一小盘青菜,便心满意足地吃着,我有些羡慕她了。
而此时,我还在《自立晚报》的“食家笔记”中,写吃的专栏,一次,正写到吃猪耳朵,刀法该如何如何,竟不忍卒笔,于是,打电话跟编辑说:“我不能一边吃素信佛,一边写吃的专栏。”遂将专栏停掉,同时,又将其他好几个专栏一并停掉了。
我想,既然决心要做一个佛教徒,必须做个第一流的,首先,把一头长发剪短,跟着戒烟、戒酒、吃素,并且皈依;学习如何拿香、礼拜、恭敬供养等佛教仪式。再就是谢绝不必要的应酬,将空余的时间拿来阅读经典。
这下,我才知道,佛教除了过去我读的那些流通较广的经书外,还有《楞严经》《大宝积经》《般若经》《法华经》《华严经》《阿含经》《圆觉经》《楞伽经》……这么多长短不一的经典,一路阅读下去,心中的疑惑顿然消除了大半——原来人是可以这么壮大的,这壮大并非和山一样地坚毅、雄伟,而是可以像虚空一般,包容种种事件,所有的横逆挫折都在佛法的包容之下,变得无比的庄严,甚至,一念觉悟——当下即心即佛。的确,这才是最圆满的法宝啊!
过去,我对神秘的东西很有兴趣,所以买了一大堆紫微斗数、麻衣相法、奇门遁甲、风水地理的书来看。也经常去访问通灵人,后来发现这些都不能给我满意的答案。有一位女通灵人,因为她通灵,丈夫要跟她离婚,打电话来向我哭诉,我说你既是通灵人,就叫你的灵去把他找回来啊!然而,她的灵却办不到,可见这些神灵的能力是很有限的。
另外,前后有三个通灵人分别说出我三种前世——尼姑、道长、文学博士,指我为道长的表示,我比他高四辈,他还要称我两声师祖,我过去的弟子则遍布宝岛台湾,弄得我有点啼笑皆非,不知道信哪个人才好。
我比较想知道的问题是:宇宙天地是怎么形成的?人又从哪儿来?我为什么会是今天这样的我?为什么会是一个作家?我的父母、环境并没有提供这样的条件啊!在我们身心感受到的世界之外,是否还存在有其他的世界?但是,这些通灵人的神通总有个极限,遇到比较有深度的问题,有的立刻呆掉,有的则层层转报,直到最高级的灵降身,仍然回答不出个所以然来。
这些疑问,在佛经中却都有了圆满的解答,使我对佛教的理论基础充满了绝对的信心。跟着我和太太便在家中设置了简单的佛堂,每天供养礼拜,并也有一些感应产生。这些感应和我小时候在庙里看到的神迹不一样,比如就买了一束玫瑰花,一半插在客厅,一半供在佛堂,客厅的花已经凋谢,佛堂的却鲜红依旧,连水也是香的,水果亦然,并且我和太太经常闻到浓郁的檩香味。这些感应,并不是那么奇特,却令我有平静的感觉。
然后,我就开始规定一些功课,每天念心经、大悲咒、拜佛、诵经。这时,在特别的因缘中,认识了我的学佛老师廖慧娟,跟随她学禅定与般若,心性与智慧都有了很大的开启。
透过这些修行的恒课,更贴切地印证了经书上所说,而这是一个不信佛的人无法理解的。我经常比喻给朋友听,我以前读经,就像是看一杯木瓜牛奶,隔着玻璃去分析它的成分、甜度、营养价值,现在看经,有如喝一杯木瓜牛奶,这其中的滋味,更与何人说?
常常我一出门,看见满街上的人,悲心便油然而生。这么多的人,这么苦,他们却不知道,每天还以苦为乐。看见昔日的朋友,仍然在大吃大喝,互相灌酒,内心不禁倍感同情,却又束手无策。有一回,进到食品店买东西,立刻难过得作呕,怎么会臭成这个样子?以前最爱吃的肉松、肉脯,怎么一下子变得奇臭无比呢?
我的朋友问我:“你在外面吃素,回家是不是偷吃蹄膀?”我说:“当我看到桌上的猪肉,就仿佛看到了一只活生生的猪,正被宰杀、凌迟,既血腥又残酷的场面,你想想,我哪还可能吃得下呢?”此话一出,听得朋友大倒胃口。
对于家里的蟑螂、蚊子,我们也开始戒杀。说也奇怪,以前是越杀越多,现在反而都不见了,我那两岁半的儿子跟着我们吃素,他看到蟑螂、蚊子,会对它们说:“你吃饱了赶快到别家去!”
信佛之初,我曾很积极地想传扬佛法。后来知道该顺其自然,不要强迫别人来信,要在别人因为你的改变,主动询问时,再告诉他佛法的殊胜,否则,你还没来得及把菩萨道的观念传播出去,别人已经被吓跑了。
比如有人问我何以近来身体越来越好?我就说因为我不喝酒,不吃肉不做伤害自己的事,并且打坐,保持心情平静,减少物欲的干扰,而这一切都得自于佛法。如果他再问我,该如何学佛,做一个佛教徒?我便进一步告诉他,学佛没有简单的方法,你必须先皈依三宝,常随佛学,跟随佛菩萨的足迹前进,要把所有的出家人当成老师,相信佛法是完美无缺,无与伦比的,超越世间一切知识,而不是去怀疑辩证。并且除了读诵经典外,还要学习修行的方法,按照菩萨道的六波罗蜜去努力实践……
我在耕萃文教院的写作班教课,就有好几位学生,因我的改变开始吃素,那里的神父也来向我询问佛法。天主教台北市修女会,请我去演讲,对象都是修女。我本来很心虚,不敢答应,经太太鼓励,只要对佛教有信心,佛菩萨会加持你的。当时,德蕾莎修女正好来华访问,所以第一句话我说:“在我的眼里,德蕾莎修女是一位菩萨!”我接着便叙述菩萨所应具备的条件,以及菩萨精神,并建议他们,如果要做一个中国的神父或修女,却不了解佛教对中国人的影响力,那将是无法成功的。
我有一些朋友,他们喜爱佛经的道理,也坐禅,却不愿把脸皮撕下来,从最卑微,最平凡的跪拜、拿香开始。也有人虽然私底下非常虔诚,却不敢公开表明自己是佛教徒。
我觉得既然信仰了佛的教化,就必须要光明正大,庄严无畏,佛教徒并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学佛的目的,主要是破我执,我执不破,打坐何用?讲经说法何用?又如何能度众生呢?因此,有人跟我说:“佛教里,我只把释迦牟尼看在眼里,其他皆不足观!”我便回答他:“我连十八王公都看在眼里呢!这些神道你都要尊重他,才能一步一步慢慢往上爬。甚至于要把一切苦难的众生都放在眼里,去救拔他们,否则,这个世界如果只有你,你如何发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菩提心呢?”
——原载一九八五年十月、十一月《人生》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