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像一道电光,曾经照亮过这个角落,又倏地消逝了。
这是我们的角落,斑驳的墙上没有窗户,低矮的屋顶上尽是灰尘结成的网。我们喜欢这个角落。铁子说这儿避风,克俭说这儿暖和,我呢?我什么也没说。我只是想离窗户远一点儿,眼不见心不烦——从那儿可以看见一所大学的楼房,一个歌舞团的大门和好几家正式工厂的烟囱。我们喜欢这个角落,在这儿才可以感到一点儿做人的乐趣;这儿是整个“五七”生产组最受人重视的“技术角”。铁子把仕女的图样设计得婀娜窈窕,大妈大婶们才能整天在那些仿古家具上涂涂抹抹,然后只有我和克俭能为仕女们长上脉脉含情的五官。大妈大婶们都很看得起我们,“啧啧”地赞不绝口。
“到底是年轻人哪!”
克俭得意地吹起了口哨。
“咱们生产组可离不了你们。”
铁子舒心地点上一支烟。
“就是正式工厂真的要你们,咱也不能给!”
我说:“那公费医疗呢?工资还是一天八毛?”
“就你矫情。依着我们还不好办?我们都是有儿女的人……”一个大妈竟擦起眼泪来。
我们哼起了《菩提树》,互相谁也不看谁。
门前有棵菩提树,
站在古井边,
我做过无数美梦,
在它的绿荫间。
……
这深沉的旋律能够安慰心灵。我想,铁子和克俭一定也和我一样,想起了那梦一般的童年和那梦一般的插队生活,在陕西,在东北和内蒙古……
我们?我们是怎么回事?唔……
清晨、晌午或者傍晚,你会在这条幽深的小巷中看见我们。我们三个结队而行,最怕碰见天真稚气的孩子。
“妈妈你看哟!”
我们都低下头。
“叔叔们受了伤,腿坏了,所以……”
铁子把手摇车摇得飞快,我和克俭也想走快些,但是不行。
“瘸子吗?”
母亲的巴掌像是打在我们心上。
这最难办,孩子无知,母亲好心。如果换了相反的情况,我们三个会立刻停了下来,摆开决死的架势……还有什么舍不得的么?那些像为死人做祈祷一样地安慰我们的知青办干部,那些像挑选良种猪狗一样冲我们翻白眼的招工干部,那些在背后窃笑我们的女的,那些用双关语讥嘲我们的男的,还有父母脸上的忧愁,兄弟姐妹心上的负担……够了!既然灵魂失去了做人的尊严,何必还在人的躯壳里滞留?!我不想否认这世间存在着可贵的同情。有一回,一个大妈擦着眼泪劝我说:“别胡想,别想那么多,将来小妹会照顾你的,她不会把哥哥丢了……”我不知当时我的脸色是什么样子,那个大妈哆哆嗦嗦搂住我,一个劲儿叫我的名字。天哪,原来这就是我活在世上的价值!废物、累赘、负担……没有人相信我们可以独立,可以享受平等,就像没有人相信我们可以得到正式工作一样。可我们的仕女图画得并不比那些正式工人画得差,画得少。我们忍着伤痛,付出比常人更大的气力,为的是独立,为的是回到正常人的行列里来,为的是用双手改变我们的形象——残废。
“算了吧,”铁子对我说,“等到二老归西,难道咱们还那么不知趣地活着?”
“弄个炸药包,和他们同归于尽!”克俭说。
“和谁?”
“谁冲咱们翻白眼就和谁!”克俭把拐杖使劲往地上一杵,险些摔倒了。
幸亏人可以死。我们好像什么都不怕了,哼着歌走在小巷深处。
今天像往日一样,
我流浪到深夜,
我在黑暗中行走,
闭上了我的两眼;
……
春风乍起,吹绿了柳条的时节,她来的。
“我叫王雪,我坐在这儿行吗?”她走进了我们的角落。
“当然。”
“只要你乐意。”
“有什么行不行的?”
我们每人一句,都是冷冰冰的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腔调。克俭在我耳边嘀咕了一句什么,不外乎“德性”“臭酸相儿”一类的评语。铁子冷酷的目光在眼镜后面闪了几下,“哼”了一声,低下头去。这是一种防御,一种以攻为守式的防御,防御什么呢?
她是一个相当漂亮的姑娘。
“你也是病退回来的?”我问。
她摇摇头:“我是困退回来的。”
“你干吗不去正式工厂?”我的语气就像是在说:“您何必屈尊到这个角落里来呢?”
“待分配,和你们一样呀!”她总想朝我们笑一笑,但都被我们依次“抵抗”了回去。
“和我们一样?”铁子冷笑了一声,没抬头。
她朝大妈大婶群里望了一眼,说:“你们不也是待分配的知识青年吗?”
我们谁也没吭声。待分配?天知道我们待了几年了。像处理西瓜似的被人扒拉过来扒拉过去,拍拍听听,又放在了一边。最后我们就“来自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来了”——有了我们的角落。
“我先坐在这儿看看你们是怎么画的。”她终于有机会朝我笑了一下,大概是因为我在我们之中还算好惹一点儿的。
角落里静悄悄的。那所大学里在做广播体操。
她把头和铁子挨得那么近;她的肩和克俭的肩碰在一起了。这两个蠢家伙,竟像是两个大气不敢出的小学生!刚才的威风哪儿去了?我想笑。他俩都没闯进过姑娘的心,都还没来得及和姑娘挨得那么近就……只有我,但那也都是往事了。
克俭一连画坏了好几笔;铁子把仕女的头发画得像拆下来的旧毛线。我脑子里一下子闪过好多往事,都是什么呢?好像又是那封信……
但她突然“咯咯咯”地笑起来了。
我们尴尬地抬起头。
她还在“咯咯咯”地笑。
铁子脸上最先出现了恼怒。
“我能看见我的鼻子!”她说,“我正看你们画画,就看见了我的鼻子,原来人可以看见自己的鼻子!”她那大而黑的眸子对在一起,轻轻地晃着头寻找鼻子,依旧“咯咯咯”地笑个不停。
我们都笑了起来。角落里吹来一阵轻松的风,好像还有一点儿温暖。
春雨蒙蒙,天空里闪过一道电光,搅动了三颗枯萎的心。
我们的角落里从早到晚萦回着歌声:《菩提树》《土拨鼠》《命运》《茫茫大草原》……先是轻轻地哼,后是低声地唱。我看见铁子认真地控制着自己的口型,克俭竭力压低自己的下巴颏,为了使歌声更低沉浑厚一些,似乎那样更能显出男子汉的气魄。我偷眼去看王雪。我发现铁子和克俭也在偷偷地看她。王雪随着我们歌声的节奏轻轻地晃着头,两个小辫一个弯了一个直,一个直了一个又弯。我们的歌声更响亮了。
老人河,啊,老人河!
你知道一切,但总是沉默,
……
“你的嗓子真好,男低音!”王雪忽然说。
我们三个一齐望着她。
“你。”
“我?”
“就是你!”王雪被逗笑了。
铁子和克俭向我投来羡慕的目光,我不敢说其中没有一点儿嫉妒。
“你们干吗光唱这些让人伤心的歌?”
“你爱听什么?”克俭说。他的脸红了一下。
“《晒稻草》,我最爱听胡松华唱的《晒稻草》。”王雪清了一下喉咙唱起来。
我们从早到晚在一起把稻草晒干,
你在那边我在这边,两人相距很远。
……
我又想起了那封信,那是一个好心人写给我心上的姑娘的……算了,不要想那些过去的事吧。
她爬到赶车台上去,让妈妈上草堆,
她在那边我在这边,两人快乐向前。
王雪还在轻轻地唱,随着欢快的节拍摆着两条小辫。
我们三个干脆停下了手里的活,愣愣地看着她,目不转睛。心中的防御工事已经拆除了,没有进攻,没有退守,没有伪善也没有卑屈……心就像和平的蓝天,就像无猜的童年;眼前出现了一泓春水,闪着无数宝石一样的光斑,轻轻拍打着寂寥的堤岸。她长得多美!但并不像那些做作的演员,用浓眉大眼招待观众,用装腔作势取媚邀宠。她怎么说呢?长得真实。她的心写在脸上,她看得起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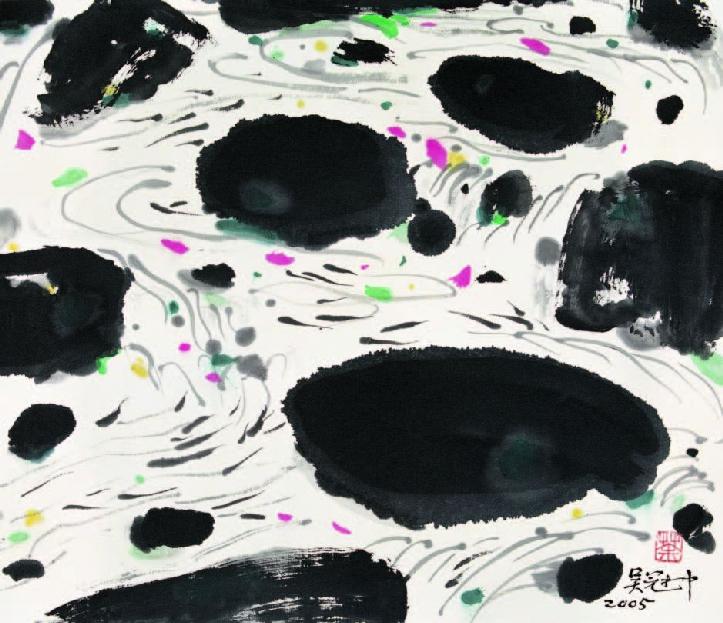
忽然铁子唱起了那支歌。
我愿做一只小羊,
跟在她身旁。
我愿她那细细的皮鞭,
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
王雪像听了侯宝林的相声似的大笑起来,笑得喘不过气,笑得弯了腰。“什么破歌呀?!还有愿意挨鞭子的哪?肯定是你瞎胡编的……”她那样随便地拽住铁子的胳膊,摆着、晃着。
她可真不像有二十三岁了,她还像个小姑娘呢。
正像歌中唱的那样,我们从早到晚在一起。我们边唱边画,边画边唱,唱《晒稻草》,唱《友谊地久天长》,唱《哎哟,妈妈》,唱那些欢乐的歌。我们的产额天天在增长,令大妈大婶们惊讶。王雪贪婪地学着,我们争着把看家的本事都端出来教她。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三个都用了长辈似的口吻和她说话,不是教训,是——譬如:
“王雪,你考大学吧,你别像我们似的。”
“王雪,你应该学外语,当翻译。”
“王雪,你不如学小提琴,只要下功夫准行。”
“王雪,你得注意锻炼身体。”
“王雪,你要记住‘防人之心不可无’。”
“王雪,晚上回家走大街,别走那些小黑胡同。”
……
王雪每天提前半个多小时就来上班,打扫车间,打扫我们的角落。灰尘结成的网没有了,斑驳的墙上挂上了漂亮的年历。遇上一天她来晚了或是请了假,我们就总会念叨她,角落里就没有了歌声,我们就又想起了招工干部挑剔的目光和母亲脸上的忧愁。那些日子,我们生活中的全部乐趣更是都在这个角落里了,但要有王雪,只要有王雪,只能是王雪。为什么呢?我还没来得及细想。
我们三个也都早早地就来上班了,而且一天比一天早,一个比一个早,而过去我们都是踩着铃声走进角落的。开始我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为什么。当我发现我们三个之间出现了一种隔阂的情绪时,我才明白了,那是由不自觉的嫉妒造成的,我们都想和王雪多耽一会儿,一天八小时太短了!而嫉妒说明了什么呢?有一次铁子和克俭竟吵起架来,无非是要在王雪面前证明自己的见解是对的。年轻人啊,残废了,却还有一颗年轻的心在跳!
我感到了这个,不那么早早地去上班了。不,我绝不是小说中那种高尚的情敌,正是因为我深深爱上了王雪,心上的防御工事就又自然地筑起来了——那是一道深壕沟,那是一道深深的伤疤,那上面写着三个醒目的大字“不可能”。何况还有那封信呢?那封信……哦,心在追求人间仅有的一点儿欢乐的同时,却在饱受着无穷痛苦的侵蚀,这痛苦无处去诉说,只有默默地扼死在心中,然后变成麻木的微笑,再去掩饰心灵的追求。
铁子和克俭也都不那么早地来上班了,因为一个大婶无意中说了一句话:“自打王雪来了以后,你们也都不睡懒觉了。”唉,他们和我一样,我敢打赌!
王雪可真还是个小姑娘呢,她一点儿也看不出这些细微变化的原因。
夏天的晚上,她央求我们和她一块儿去附近的小公园看露天电影晚会。
她举着已经买好了的四张票,说:“《玛丽亚》,可好看了,去吧!”
“我不爱看电影。”铁子说,“那样的电影,看完了三天都堵心。”
“那咱们看《甜蜜的事业》,同时演好几部呢。”
“我也不去。”克俭说,“甜蜜啥呀?甜蜜个屁!”
“那你去吧,啊?”她又对我说,“散了电影,路可黑了……”
“你害怕吗?”我们同时问。
她皱着眉,难为情地点了一下头:“嗯。”
我们都同意陪她去了。因为能保护她,我有一种自豪感;铁子和克俭大概也是。
小公园里晚风习习,凉爽,飘着阵阵清淡的花香。多少年了?五年了!自从架上这两只拐杖我就再没来过这儿。来这儿干什么呢?只能勾起往事:这儿是我童年时代的乐园,欢歌笑语恍如昨日;这儿遗留着我少年时代的希望,不过已经认不出哪棵白杨是我栽下的了;那片草地上曾有过一群即将去插队的青年,用心里涌出的朴素无华的诗句讴歌美丽的理想……可是后来呢?
天还没黑,银幕前只坐了几个孩子,仰着小脸望着空白的银幕。他们怎么会那么有耐心?噢,他们会幻想出五彩缤纷的画面,去填补空白的银幕。他们还太小呢。
铁子和克俭也都沉默着。
王雪哧哧地笑起来。
小树林里对对情人在漫步,在依偎,在亲吻。
“你别笑,将来你也那样。”我不知怎么竟会说出这样的话。
王雪满脸绯红。“去你的,我才不呢……”她嗫嚅地说。
唉,还是别想这些的好。
可是铁子又冒出了一句不该说的话:“王雪,你跟我们在一起走不嫌寒碜吗?”
“寒碜?为啥?”王雪一跳,揪下了两片树叶,淘气地塞进了克俭的脖子。
“你不怕吗?”我问。
“怕?怕啥?”
我没法回答她了。那封信!那封信是这样写的:“你不要和他来往过密,你应该慢慢地疏远他。因为他可能会爱上你,而你只能使他痛苦,会害了他。”那时我就懂了,我没有爱和被爱的权利,我们这样人的爱就像是瘟疫,是沾不得的,可怕的。我就离开了我心上的姑娘。她现在在哪儿呢?
“怕啥吗?问你!”王雪在我肩上捶了一拳,手里托着一只花牛牛。啊,但愿你永远像个小姑娘。
“噢,我是说天黑了,你不怕吗?”
“去去去!”她不好意思了。“我们看《甜蜜的事业》还是看《三笑》?”她打岔说。
又是克俭说:“三笑?笑个屁!”
铁子说:“看《猎字九十九》吧,图个热闹算了。”
“不!我想看《甜蜜的事业》。”王雪站住不走了。
“那你一个人去看吧,散了电影一个人回去。”铁子故意逗她。
她不言语了,捧着花牛牛委屈地跟在我们身后走。
我真有点儿可怜她,但铁子和克俭忍着笑冲我挤眼。我忽然觉得世界是那么美好、甜蜜,我们像三个顽皮的小哥哥,逗弄着一个可爱的小妹妹。
她可真像是个小妹妹。一演到打斗和紧张的地方就闭起眼睛,紧抓住我的拐杖,或者嘟嘟囔囔地埋怨铁子和克俭。我有个强烈的愿望:时间停下来,让她永远是个小妹妹,让我们永远做她顽皮的小哥哥,永远这样相处在一起,忘记过去、现在和将来,忘记一切……有一次我真的忘记了我自己:为了去捡王雪掉在地上的毛线团,我的手竟离开了双拐,像健康人那样去追赶、弯腰伸手,“啪!”我的胳膊摔破在石头上……我愿意再摔十次,因为王雪当时心疼得快要哭了,是我满不在乎的样子才又使她破涕为笑。
人们说,爱情是压制不住的。真的,只需要找一个借口,理智就会服从感情,什么“决心”之类就都忘到九霄云外去了。那个夏天,在那个小公园里,我们一起度过了好多个甜蜜的夜晚。借口就是:在漆黑的小路上我们得保护王雪,得把她送上回家的汽车。都看了些什么电影,记不得了;只记得落日、晚风、明月、繁星和那个不把我们另眼相看的“小妹妹”。
秋风起了,吹黄了小路两旁的草丛,吹谢了草地上的野花,吹光了小树林的茂叶,吹去了小公园里甜蜜的夜晚……如今想来,那只是一场梦。

一天,王雪忽然发起愁来,独自默默地发呆,叹气,好像一夜之间变成名副其实的大姑娘了。
“你怎么了?”铁子问。
她看看我们,想说又没说。
“你病了?”克俭问。
她想说又没说,脸上起了一片红晕。
“有什么难事告诉我们,谁欺侮你了?”
“谁活得腻歪了?谁?告诉我!”克俭把手指弄得“嘎巴巴”直响。
“没有谁欺侮我。”她吞吞吐吐起来,“是妈妈,妈妈非让我见那个人不可……”
角落里静极了。
“是二姨给我介绍的,一个大学生……”
听得见风把电线刮得呜呜地响。
虽然这是早已想到了的事,虽然我早就筑起了护御工事,但我的心仍像掉进了一眼枯井,往下掉,忽忽悠悠地往下掉……我说不清那一瞬间都想了些什么。好像只想着明天,明天可怎么过呢?我还能拄双拐兴致勃勃地朝这儿走么?希望,尽管那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希望,但是没有它是多么可怕!我迫切地想要一支烟……铁子和克俭已经点起了烟,把打火机递给我……“扑通!”我的心摔在了漆黑的井底。我真想就永远待在这井底,忘记世界,也让世界忘记我……
然而王雪那求助的目光望着我们,像一个信赖我们的小妹妹那样。“我应该去见他吗?”她说。
王雪是个好姑娘,她应该享有比别人更多的幸福,她最应该!她单纯,不会想到要避开我们,难道因为这个我们反而要影响她的幸福吗?难道好人只有用牺牲去证明她的好么?难道幸福只是为那些把我们另眼相看的人预备的?我们的心灵不是在顽固地追求么?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我不想见,有啥意思……”
她在盼望我们的帮助,她需要我们的帮助,因为她还像个“小姑娘”呢。原谅我刚才那一瞬间的罪过吧,我是多么自私。
“你应该去见。”铁子最先缓过劲儿来。
“爱情是有意思的。”我说。
“就是!”克俭也说。
“处理得好,爱情会使你幸福,对工作和学习都是一种促进力量,世界都会变得美好起来……”我是在背书么?但书的作者未必有我体会得深。
我们三个都一本正经起来,谁也不说谁“酸文假醋”“装蒜”或“瞎掰”——像三个称职的哥哥似的。我奇怪我们都能说出那么像样的爱情伦理,唔,只不过是因为我们过去都像是那只吃不到甜葡萄的狐狸罢了。王雪那么出神地、松心地、信赖地听着我们的“爱情伦理学”。她佩服我们了,她更看得起我们了,她眼睛里的闪光告诉了我们这个。我们被一种自豪感驱使着,为了无私地爱护着一个“小妹妹”。
但是,那天晚上我们又结队走在幽深而寒冷的小巷里的时候,我们又唱起了那支一夏天都忘记了唱的歌。
今天像往日一样,
我流浪到深夜,
我在黑暗中行走,
闭上了我的两眼,
好像听见那树叶对我轻声呼唤,
朋友,回到我这里来找寻平安。
我们又都早早地来上班了。不,跟过去不同,我们三个之间谁也不嫉妒谁,只是想和王雪再多待一会儿。因为她的男朋友有办法给她安排一个正式工作,王雪要走了,要离开这个角落了。她说以后还会来看我们。我们的心还要什么呢?在这世界上?
冬天,王雪当上了正式工人。她去报到的那天,我们三个冒了小雪又去了一次那个小公园。
雪花飘呀飘,像我们那紊乱的心绪,雪花无声地落呀落,世界是那样孤寂。
我们互相搀扶着走,小路上留下了奇特的脚印和车辙。这小公园里,好像到处都有她的歌声。
我们从早到晚在一起把稻草晒干,
你在那边我在这边,两人相距很远,
……
我用手去接那晶莹的雪花,雪融化在掌心里,像一滴泪。
她像一道电光,曾经照亮过这个角落,又倏地消逝了。我们祝愿她幸福,她是个好人。
一九八〇年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