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发现它,现在回想,大约是三年前一个闷热的傍晚,在下城6号地铁第三节车厢,刚离开28街可是还没有进入23街站,背靠着中间车门,正在没有什么目的也没有任何意识地抬头遥望对面车顶之下一张张医治脚气、安全性行为、隆乳、减肥广告的一刹那,我突然发现其中有一首两行诗:
先生,你也凶悍,我也凶悍,
可是谁来写谁的墓志铭?
作者是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后来才发现这是一首经过本人特许之后才首次在纽约地下铁上发表的诗作。
自从那个傍晚之后,无论我搭乘纽约任何一号地铁,或任何一号公车,我都看到有这位那位知名或(我)不知名的诗人的作品,印在和一般标准广告大小的海报式纸板上,张贴在车厢刊登广告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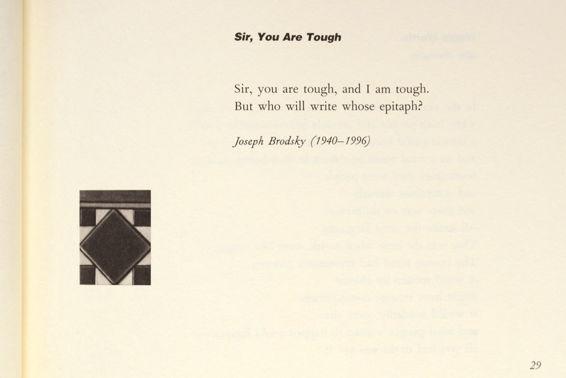
“先生,你也凶悍,我也凶悍,可是谁来写谁的墓志铭?”,约瑟夫·布罗茨基, 1991,地铁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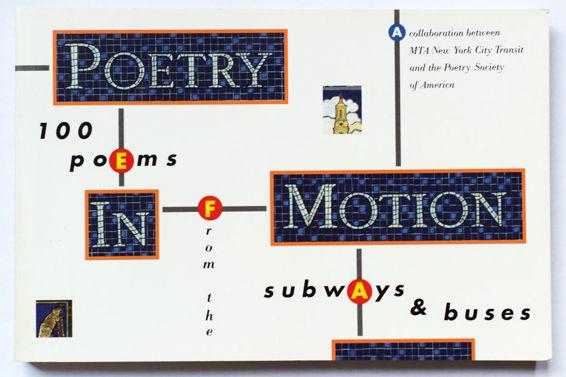
诗册封面
我同时又发现,这些车厢中一系列的诗歌还有一个称号,叫做“流动的诗”(Poetry in Motion),是纽约市捷运和美国诗会合办的,献给所有乘客。
连我这个从来没有写过诗,而且只不过极其偶然才读几首诗的乘客,都感动地设法利用乘车的有限时间,去看、去默记几首短诗,或一首较长诗作之中几个短句:
你问我在想什么,
在我们是情人之前。
答案很简单,
在我认识你之前,
我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想。
很美吧?但英文原诗更美。因此我要在此向作者Kenneth Rexroth和读者致歉,我只能以散文体来表达。至于我写诗的朋友,我想他们不会怪我,这些都应该是他们非常熟悉的名家名作。
地铁公车上有诗?我觉得这是纽约捷运全部冷气化之后最伟大的贡献。
公共交通系统转载诗歌并不是纽约的新概念,欧洲十几年前就开始了,而旧金山的巴士也早在1984年就在车内张贴诗作。不过,纽约是因为地铁总裁发现伦敦地铁这么做才建议仿效的。今天,纽约市四千多辆地铁和三千七百辆公车里面,每一个月轮换两首不同的诗,而且今年6月还出版了《流动的诗》选集,共一百首。
纽约的反应好像非常之好,地铁乘客好像也很高兴。想想看,在世界各地都放映的好莱坞电影的描写之下,纽约地下铁简直是通往地狱的运载工具。因此,当我们在地铁看到了但丁在《地狱篇》中说,“在我们生命旅途的中间/我发现我迷失在一座黑暗森林之中/找不到那条大路”的时候,不论我们多么失意失落,至少不会感到孤独,何况再有两站就到家了。
再有两站就到家,这也许是你我看了但丁那首诗后在地铁上的反应,可是女诗人May Swenson并不这么认为。她在地铁上那首《搭A号车》中觉得,“轮与轨顶顶相碰/在滑动油润摩擦中做爱/这是我愿延长的欣快/站抵达得太早了”。
诗人和爱诗的人也许早就认清了一点,而我却是在纽约地铁上受到这些“流动的诗”启发的,就是,诗的确要比散文更能不浪费任何文字地抓到重点。你看Stephern Crane的《一个人对宇宙说》:
一个人对宇宙说:
“先生,我存在!”
“但是,”宇宙回答说,
“这个事实并不使我产生任何义务感。”
我们二人的差别不光是他是19世纪的人,我是20世纪的人,而且他是先知,我是后觉。然而,就在我发现我之存在与否,对宇宙来说完全没有意义之后不久,我在地铁上(真不好意思)又发现了比他晚一代的Edna St. Vincent Millay的颂歌:
我们很累,我们非常快乐幸福——
我们整晚来回乘坐摆渡;
从我们不知哪里买的各一打里,
你吃了个苹果,我吃了个梨,
天空泛白,冷风呻吟,
太阳冉冉升起,一桶黄金。
不知道这一对显然正在热恋中的情侣,有没有(当然不是在地铁上)读到与其创作者同时代的另一位诗人作家Dorothy Parker的《不幸的偶然》:
当你颤抖叹息地
发誓说你属于他,
而他也誓言他的热情
无限而不朽——
夫人,请注意:
你们有一个在说谎。
唉!在纽约坐了这么多年的地下铁,我发现我除了担心被偷被抢之外,最近又多了一层烦恼——是吃苹果的在说谎,还是吃梨的在说谎?再又因为发现了我之存在与否,宇宙丝毫没有义务,那我只能暂时忘记存在和爱情,而回到更基本迫切的现实:在闷热夏夜搭乘纽约地铁,我要冷气,不要诗。
什么?你说我小看诗人?瞧不起诗?先生,你也凶悍,我也凶悍,可是谁来写谁的墓志铭?
1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