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受害人的尸体被弃于“请勿投掷”区域,反映了连环杀手典型的自大与敌意的心理

图为连环杀手嫌疑犯杰勒德·谢弗被佛罗里达州警方带出审讯室。注:图中唯一一个神情轻松的就是嫌疑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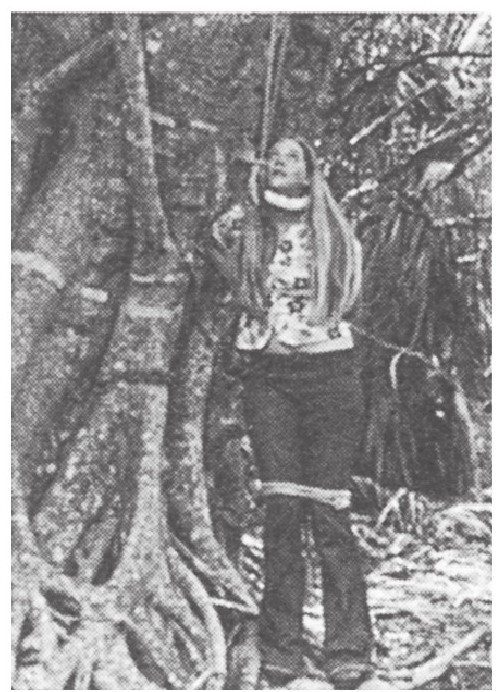
从杰勒德·谢弗手中死里逃生的被害人向警察模拟她的受害过程

赫伯特·M.马林,在加州圣克鲁斯附近杀死14个人的连环杀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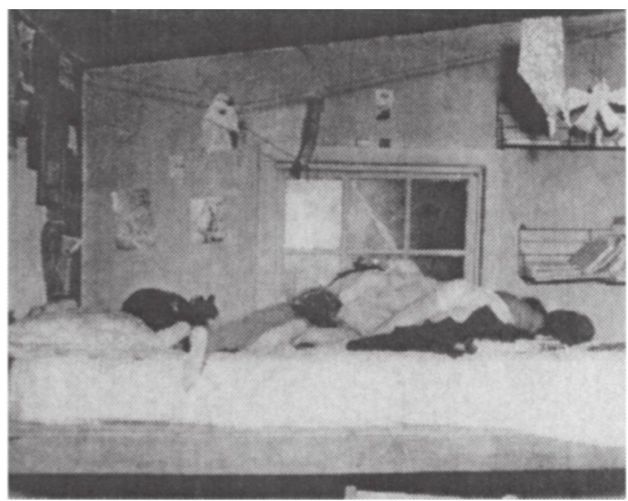
疯子马林的受害人
多数人看到暴力犯罪的证据时,都会表现出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他们无法理解凶手的行为,普通人很难从尸体或其他线索追查下去,查明案情,很多警察也是如此。这其实并不奇怪,因为他们经验不足,不了解这些凶残的疑案是那些奇特的杀手所为。但对我们而言,这些谋杀案发生过很多次,只要分析正确,我们就可以充分了解犯罪的模式和细节。
到20世纪70年代末,行为科学调查组已经利用这些犯罪的资料累积了大量的经验。普通警察也许一辈子都不会碰到这种吃人、分尸等令人发指的暴行,因此遇到这类案子只有移交给联邦调查局去分析、侦办,我们把所有的资料综合整理分析之后,就可以分析凶手的行为模式,并有助于此后类似案件的侦破。
研究资料和把这些资料应用于警方的侦破工作是不同的两种事情,我们向警方解释的时候必须避免使用晦涩的心理学术语,这样才能让执法机关充分了解凶手的特征,如果讲解得过于专业,则会造成理解上的困惑,因而我们必须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警方描述凶手的行为模式,这样才能帮助他们找到真凶。
上文说过暴力型罪犯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事先策划、按部就班、冷静执行、条理清晰的罪犯,我们称之为“有组织罪犯”;与之相反的是杂乱无章、行事莽撞、随机行事、出其不意的罪犯,我们称之为“无组织罪犯”;有些罪犯同时兼具两种特征,我们称之为“混合型罪犯”。举例来说,埃德蒙·肯珀是“有组织罪犯”,但他分尸的行为又属于典型的“无组织罪犯”的行为。
接下来我就开始说说这两种凶手的特征,但我必须先强调一下,我说某人属于“有组织罪犯”并不代表他的行为在任何时候都是“有组织”的;我说某种行为是“有组织罪犯”的典型行为时,也不表示所有的“有组织罪犯”都有这种行为。举个例子,掩藏尸体是“有组织罪犯”的典型行为,但我们在访谈及命案现场分析中发现只有四分之三的“有组织罪犯”会做出这种行为。另外,心理侧写也是如此,并不一定完全准确。两种罪犯的差异很明显,但两者之间依然存在着大片交叉区域。
要想判断凶手属于哪种类型的罪犯,必须依据现场的照片。如果可以的话,最好也查看一下从被害人身上取得的证据以及别人对被害人的描述,这是为了评估凶手作案的风险,如果被害人是老人或小孩,那凶手的风险自然大减。另外还得追问被害人是如何被选中的,比如蒙特·里塞尔在天刚亮的时候从停车场劫持了一名妓女,而他挑选被害人的原因则是破案的关键所在。
一般而言,犯罪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准备阶段,凶手通常会在作案前进行一些准备,但对调查人员来说这部分通常是最后才知道的;第二阶段即所谓的实施阶段,我们在调查这一阶段时,重点会放在凶手如何选择被害人以及如何实施犯罪这两项内容上,一般这个阶段会包括谋杀、挟持、虐待、强奸等行为,杀人方法也多种多样;第三个阶段就是抛尸阶段,有些凶手选择抛尸地点非常随意,有些凶手则经过仔细的考虑以避免被人发现;最后一个阶段就是犯罪后的行为,对于某些案子来说,这一阶段尤其重要,因为有些凶手在作案后会想方设法摆脱我们的调查,甚至远走高飞,但另一些凶手则会找机会接触办案人员或者在命案现场徘徊,也可能接近被害人葬礼、墓地,这种人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幻想。
“有组织罪犯”都是步步为营,绝不是临时起意的,因而其行为模式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对犯罪的策划。他们的策划工作主要是从幻想里来的,可能在他们远没有走上犯罪道路那会就形成了,上文中提到不少这种例子,比如朱伯特在刺死第一个人之前,这种计划就在他头脑里酝酿多时了;还有里塞尔也是如此,他在停车场因为思念女友而遐想无限之际,刚好找到了一个中意的被害人,而这种暴力幻想在很多年之前就存在于他头脑中了。
“有组织罪犯”大多挑选陌生人下手,一般是他们游荡时发现的目标。这些罪犯的心里都有挑选被害人的一些标准,比如年龄、外表、职业、发型或生活方式等,戴维·伯科威茨就专找独身的开车女性或与男友同车的女性,而且总是在停车场作案。
这种凶手通常运用一些策略来欺骗被害人,他们大多数都非常聪明,而且能说会道,能够吸引被害人跟着他们到隐蔽的地方。控制被害人对这些凶手来说极其重要,执法人员后来专门学习了这些凶手的种种伎俩,如凶手会塞给妓女一张50美元的钞票;装好心人让被害人搭便车;帮助一个受伤的摩托车骑士;骗小孩说带他去找母亲等。他们在实施之前经过详细的策划,事先充分谋划了如何骗取被害人的信任,并不断完善他们的诈骗技巧。比如约翰·加西在芝加哥同性恋者聚集地用钱吸引被害人,他声称如果有人愿意跟他回家做爱就付钱;特德·邦迪以自己英俊的样貌勾引妇女上车等。
相较之下,“无组织罪犯”在选择被害人的时候就毫无逻辑,因此他们作案的风险更高。比如,他们选了一个强壮的对象,对方就会反击,因此这类罪犯的身上多有一些自卫造成的伤痕。另外,这种罪犯对被害人本身毫无兴趣,也根本不关心对方是什么样的人,只是想快点打昏他们或者想方设法不让对方看到自己的脸。
前面提到“有组织罪犯”的主要特征就是精于策划,这表明他们的犯罪行为的所有阶段都被精心安排好了,一步步走下去即可;而“无组织罪犯”的行为则显得杂乱无章,很多事情要到我们逮捕他并得到他的口供后才能明白,但即便如此,我们依然可以根据线索把侦破工作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来。
在实施犯罪的过程中,“有组织罪犯”能够随机应变、保持镇静,比如埃德蒙·肯珀在一所大学校园内枪杀了两名女学生后,还能神色自若地开着装有被害人的车经过警卫身边,后来他说自己当时也很紧张,但并没有表露出来。如果是一个“无组织罪犯”遇到这种情况,他可能惊慌失措、坐立不安,只想尽快地逃跑,这样反而会引起他人的注意。
我们可以看到,适应能力及随机应变的能力是前者的特征,也是他们最厉害的地方,有些罪犯从一次次的犯罪中学习到了很多东西,并日益增进其杀人技艺。因而,如果警方发现了五起特征相同的连环杀人案时,我们会建议他们全力侦破第一件,因为时间越早的案子越容易露出破绽,比如凶手第一次行凶时可能选择离自己较近的场所,但后来就会越离越远,因此侦破第一件案子的概率最大。
我在上一章提到自己利用凶手日益进步的犯罪技巧逐渐修正我对凶手的侧写,并因此抓住了约翰·朱伯特。这种案子还有很多,比如蒙利·里塞尔。他被捕后供认自己在十几岁的时候就犯下五六桩强奸案了,最开始他是在自己的屋子里作案,后来开始挟持女性到对方家中作案,最后他更加“进步”,开始开车到其他州作案。随着时间的推移,每次案件的证据越来越少,最后警方把主要精力都放到最开始的几桩案件上,发现他那时候总是挑选离自己家很近的女性下手,这才抓住了他。他杀人的暴力程度越来越高,比如那五六桩奸杀案中,前三个案子都是先奸后杀,后几个案子则是先杀人后奸尸。
有时候,“有组织罪犯”的策划过于精细,反而可以让警方找到线索,比如凶手一直使用相同的行凶工具(手帕、绳子之类),就容易被警方顺藤摸瓜。
交通工具也是我们判断凶手特征的重要线索,他有没有使用交通工具,或者用了谁的交通工具都是重要线索,比如蔡斯凶杀案发生时,我对警方说凶手可能是步行到现场作案的,这说明凶手就住在附近,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从线索可以判断凶手是个“无组织罪犯”,他有严重的心理疾病,因此他不能在控制被害人的同时开车。读者如果记得第一章的内容,就知道我提出凶手住在附近这条推论对最终破案非常有用。像蔡斯这种“无组织罪犯”一般是步行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到达现场的;而“有组织罪犯”则一般会开车或开着被害人的车去作案,这么做是为了毁灭证据。“有组织罪犯”自带武器去作案,案发后绝不会留下凶器,因为他知道凶器上的指纹或弹道都可能让他暴露,带走凶器是最安全的做法。另外,他会抹去作案现场留下的所有指纹,并清除血迹和其他证据。对破案来说,判断死者是谁的时间越长,凶手逍遥法外的机会也就越大,因而“有组织罪犯”经常抛尸、毁容,或者丢掉死者的衣物,就是想拖延警方确认死者身份的时间。
“无组织罪犯”的心思就没有这么缜密了,他们可能随手使用被害人的刀杀害对方,凶器可能就留在死者身上,都不知道拔出来扔掉,他们想不到消除指纹这种事情,因而警方可以很快找到他们。但“有组织罪犯”会把尸体带走并找到一个隐蔽地点藏尸,比如特德·邦迪杀害的很多人的尸体都找不到了。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市有一个名叫鲍勃·伯德拉(Bob Berdella)的凶手,他的手法和约翰·加西手法类似,他在绑架、虐待并杀死男孩后,会把孩子的尸体剁成块喂狗,因此很多被害人尸骨无存。
所有的事情都不是绝对的,“有组织罪犯”中也有不少反其道而行之的案例,比如臭名昭著的“山腰绞杀手”20,他们非常自负,故意把尸体丢到警局前面示威。有些“有组织罪犯”会故意把作案现场和抛尸现场弄乱以迷惑警方,这也需要事先精细的策划,“无组织罪犯”是不会这么做的。
执法人员到达命案现场后必须能够分辨本案的凶手是“有组织罪犯”还是“无组织罪犯”。一般而言,后者的作案现场能够显示出其心理的混乱,死者一般会伤痕累累,有时候他们也会因为极度疯狂而将死者毁容或肢解,但不是为了掩盖证据。而前者则会尽量毁灭各种证据,两者迥然不同。
“有组织罪犯”一般会拿走被害人的东西当作纪念品,也可能是为了让警方找不到证据而这么做,皮包、首饰、戒指、衣物或照片等都是其下手的对象,抓到凶手后会在其住处找到这些东西。他们拿这些东西并不是为了换钱,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幻想,把它们当作自己的“奖杯”以达到心理上的满足。就像猎人喜欢在墙上挂满动物的头颅一样,凶手在观赏这些物品时心中感到无限愉悦,同样这些物品也能让他们记住被害人和犯罪经过,从而可以经常回忆往事。除了拿走被害人物品外,有些凶手会在行凶时拍下照片,道理也是一样的。有些杀手甚至把被害人的珠宝首饰送给自己的家人,他们看到这些东西时就能回忆起过去,这种隐秘的快乐让他们很兴奋。约翰·布伦南·克拉奇利(John Brennan Crutchley)最开始被起诉强奸,但我判定他是一名“有组织罪犯”,而且应该是连环杀手,因为他的卧室墙上挂了十几串项链。以前提到过的蒙特·里塞尔,在奸杀被害人之后拿走其皮包和首饰,并藏在他的公寓内,后来他的幻想更加严重,作案后甚至会开着被害人的车载着尸体兜风达几个小时之久。
“无组织罪犯”一般不会取走被害人的东西当作纪念品,但可能由于理智全失而取走受害人身体的一部分或一些饰品。
我一再强调,所有的犯罪行为在本质上都和性有关,即便作案过程中没有对受害人进行性侵犯也是如此。一个真正的“有组织罪犯”会通过多种途径完成性满足,他们可能在杀害对方之前强奸、虐待对方,也可能是通过殴打、割伤、勒死等行为完成性欲的发泄。相比较而言,“无组织罪犯”想不出这么多“招数”,他们只会奸尸或与失去抵抗能力的被害人发生性行为。
另外,两者还有一点不同,那就是“无组织罪犯”作案时非常迅速,而“有组织罪犯”作案时则会“精雕细琢”,仿佛是在创作一件完美的作品,并非常享受杀人的过程,因而他们不会直接把对方杀死,而是反复折磨。约翰·加西在真正杀掉被害人之前,会把对方折磨得死去活来,但一直留着一口气,这样他才能获得最大程度的满足。具体到强奸过程,“有组织罪犯”需要看到被害人的恐惧和不安,如果对方反抗,他们就会更加兴奋,也因此更加凶残,因此他们经常在强奸过程中把对方杀死。
在犯罪的第三和第四阶段,“有组织罪犯”会按照计划藏尸,或者利用毁容、分尸、焚尸等方法掩盖死者身份,并和警方斗智,在他的精心策划下会控制整个作案的行为,从而让警方很难破案。有一个凶手是医院救护车的司机,有一次他从一家餐厅的停车场绑架了被害人,在其他地方将其奸杀后故意把尸体抛在一个很明显的地方,然后打电话报警,等警方到来后他才走开,这样警方就不会怀疑他了。后来他发现把尸体弃置于垃圾场可以带来更大的满足感,因此就开始连续作案。
两者在人格特质上有很大的不同,而且其人格的发展过程,以及人格对其行为的影响都有很大的不同,这些对侦破工作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线索。一般而言,“无组织罪犯”的父亲通常工作不稳定,对他的管束非常严格,其家庭成员多有酗酒或精神病史。而“有组织罪犯”大多生长于小康之家,父亲工作稳定,但不大管教孩子,任其我行我素。
前文提到过“无组织罪犯”在成长过程中经常遭遇沮丧、愤怒和恐惧等不良情绪,正常人会通过与其他人的交流缓解这些压力,而他们会把这些情绪隐藏在心里,他们找不到发泄的途径,也缺乏行动和语言上的技巧,即便面对专业心理分析人员也无法清楚地表达自己的心情。他们通常长相很差,别人都不关注他们,这也是他们无法表达自己的原因之一,此外,他们身体一般很虚弱,且与旁人格格不入,而他们对自己的这种情况感到无地自容,但这个不幸的事实不会让他们奋发图强,反而使他们更加沉浸于自我的幻想中,使得他们更加伤心、生气、孤僻,变成离群索居的遁世者。因此,他们很难和一位异性同居,甚至无法找到可以同处的同性朋友,顶多是和父母居住在一起。总之,他们拒绝融入社会,非常自卑,大多不聪明。他们自认为能力不足,一辈子只能庸庸碌碌,最多打打零工而已。举个例子,有个人杀了一个年轻女子,警方侦讯时,他自称是名失业的演员,其实只不过是个舞台管理人员,而且因为无法管理好灯光而被解雇。他之所以说自己是演员,一方面是因为表达能力不足,另一方面则体现出他经常幻想。
“有组织罪犯”一般非常外向,在学校的时候通常是孩子王,经常和别人打架,有时候也会胡作非为。普通人大多认为这是凶手的普遍特征,但这种人只属于“有组织罪犯”。“无组织罪犯”在学校里一般很低调,无人注意,因此当他日后被捕的时候,同学和老师甚至想不起来他这号人,但他的邻居一般认为他是个好孩子,待人彬彬有礼,从不惹麻烦。
“有组织犯罪”则非常高调,同学们会认为他是个麻烦的家伙,总是喜欢打架、不遵守校规,他们很聪明,通常可以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但因为总惹事而常被解雇,在压力之下会走上犯罪之路。一个前俄亥俄州的警官因行为不检而经常惹麻烦,工作、感情都不如意,而且经常上法庭,在一次意外事件中他绑架了一名年轻女孩,最后杀了她。“无组织罪犯”通常不会遇到这种压力,他们是因为心理异常才犯罪的,外部世界对他们的影响不大。
上文说“无组织罪犯”总是自卑,而“有组织罪犯”则完全相反,他们自视甚高,像加西、邦迪及肯珀都是这种人,他们认为警方都是些蠢家伙,根本无法抓住他们,并认为心理学家都是些废物,根本不了解自己的想法,总而言之,他们自认为是最聪明、最成功的人。犯下罪案后,他们会关注媒体报道,而“无组织罪犯”根本不会关注这些事。
“有组织罪犯”通常有多个性伴侣,由于天资聪颖,又会花言巧语,总是能吸引异性(有时是同性)和他们上床。除了有吸引力外,他们还有很强的心理分析能力,但无法与别人维持正常而长期的关系,他们虽然有很多伴侣,但交往的时间都不长。在俄勒冈州有一个喜欢开膛破肚的凶手,他有很多性伴侣,但没有一个与他有深入而长期的关系。特德·邦迪的女人在被杀之前认为他的性能力很差,因此他对女人有种仇视的心理,而且相信是这些女人造成了自己的性无能。因此,许多强奸犯都会殴打被害人。
此外,这些人经常敌视其女友,好像女友做什么事情都是故意在与他们作对。他们的智商很高,但并不是真的聪明,否则曼森为什么不去追寻当摇滚歌手的理想呢?实际上,他们认为这个社会抛弃了他们,社会使他们堕落,因而曼森总觉得自己不该进监狱,而应该是一个红得发紫的歌手,他的这种说法很有煽动性,搞得手下那群人都奉他为精神领袖,并甘愿为其发动所谓的“阶级战争”。埃德蒙·肯珀认为自己是劫富济贫的侠客,因为他的受害人都出身于富裕之家或中产阶级,他相信自己的行为必将引来未来阶级重整的潮流。而约翰·加西则认为整个社会都是他的敌人。
在我们的研究中发现,有不少杀手兼具两种特征,我也经常对学员们强调这一点,并经常用杰勒德·谢弗(Gerard Schaefer)作为案例来解释,下面就说说这个案子。
20世纪70年代初,佛罗里达州警方接到数起妇女失踪的报案,因此马上成立了专案小组,很快就发现了线索。其中两名年轻妇女在失踪前误入沼泽地,她们发现很难走出去,狼狈不堪之际,刚好有一辆汽车出现,她们便搭便车到了城里。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一段时间以后她们在警局说出了那段痛苦的遭遇。
当时他们看到那辆车子的时候感到有救了,便叫停了汽车。这辆车看起来像是警车,司机长相很普通,衣着整洁,他说可以载两个女人到她们想去的地方,但车子开动后却往森林深处驶去。接着司机拿出枪来强行把她们捆在了一起,那个司机得意扬扬地宣布自己要奸杀她们,并说自己以前就干过很多次了。凶手实施强奸之后忽然看了看手表,说:“糟了,我得回去啦!”说完就开车跑了。
两个女人拼命解开了绳子,跑到马路上求援。她们把警察带到被绑的地点后模拟了事情的经过,在此过程中她们因为害怕而一直哭个不停,最终还是向警方说出了事情经过,她们还说凶手把她们绑起来以后,曾找来一根树干,可能是想把她们吊起来。
警方搜索了附近区域,发现一些残缺不全的腐烂尸体和一些女人衣服的碎片,鉴定后发现这和前几起失踪案中的女子所穿衣物相同,都是牛仔裤的布料。等两名女子的情绪稳定之后,警方继续让她们讲述案情的细节。两名女子说凶手的车里有个缓冲器,凶手就把绳子的一端绑在这个缓冲器上,另一端用来捆绑她们,后来凶手打算开动车子把她们吊起来,此外,她们还看到凶手的汽车玻璃上贴着一张兄弟会的贴纸。
在进一步分析前我就确定这名凶手一定是个“有组织罪犯”,因为他在作案过程中不断与被害人谈话,使用自己的交通工具,并用诱骗的方式让女人上他的车子,携带枪支并在作案后带走了它,他的谋杀很有计划——先强奸,再凌辱,最后杀害,这足以证明他是个“有组织罪犯”。我猜他打算在这次作案后掩埋尸体,但因为临时有事无法完成,令人疑惑的是什么事比杀掉两个女人、掩埋尸体更重要呢?
杰勒德·谢弗很快就成了嫌疑犯,他曾是个警察,因为以前犯过事而被警察局除名。根据他以前的同事讲,他以前经常拦下女性的车辆,伪称对方交通违规并抄下对方车牌号码,等回到警局后就从电脑数据中查出对方的电话号码和其他资料,过不了多久就会打电话约对方出来(我在这里要补充一点,有很多人也干过假借职权获取意中人资料的行为,但他们只是想和对方交往,而这些凶手则是为了把女子诱骗到树林中凌辱或杀害)。后来的调查显示,他之所以没有杀掉这两名女子,是因为当时接到另一位警察的呼叫,他们当时约好了一起赶回警局。那两名女子指证谢弗开的车子和她们看到的车辆十分吻合,警方在搜查他的住处后找到了属于其他被害人的牛仔裤。这时候,已经基本确定他就是凶手了。
谢弗坚决否认所有的指控,但证词和证据十分确凿,他还是被提起公诉,并被判刑,现在仍然在佛罗里达州的监狱里服刑。但我们永远无法知道他总共杀了多少名女子,据估计,有35人。由于他拒不认罪,且不配合警方的侦破工作,因此我们无法确定,除了被查出的案件外,他还犯过多少其他命案,也无法找出那些被害人的尸体。
从犯罪心理研究的角度看,谢弗的住处可真是资料丰富,屋子里不但有自己犯罪的证据,还有很多可以供我们研究的资料。屋内有女性衣物和珠宝首饰,很显然这是从被害人的身上拿来的,但在询问过程中他说这是自己任巡警时在高速公路上捡回来的,他本想捐献出去,但还没来得及,其中一些送了人,有一条项链就送给了女友。在他家里还发现了大量淫秽书籍和侦探杂志,他在警局的同事也证实他非常喜欢看女子被吊打、勒死之类的场景。
我们从他的日记和他家墙上的画可以看出来,他很早就开始了折磨被害人的幻想,所有这些细节都互相关联。他在墙上画的画中,有一幅画了一名年轻女子被反绑在一棵树上,身上还被打了一枪,画上甚至有女子排出的粪便。另外一幅画上有三个裸体女子面对着一个男子,旁边加了一行字:“这些女人必须取悦我,否则我就强奸她们,然后让她们到广场上去卖淫。”还有一幅画画着一名躺着的年轻女子,从侧面看就好像被吊起来一样。除了这些画作外,他屋子里还有一些他自己拍摄的照片,都是被害人被吊起来的场景。
审判期间,他经常耍弄新闻媒体,谁都无法从他嘴里套出一点信息,他只是对媒体反复说:“我是被冤枉的,总有一天会还我清白。”有份报纸刊登出一张庭审时的照片,拍的是四位法警押着他的场景,他在照片里满面笑容,气定神闲,即便是后来被判终身监禁的时候他依然非常镇静,这都是典型的“有组织罪犯”特征。
赫伯特·马林在20世纪60年代末高中毕业以前,所有住在圣克鲁斯附近并且认识他的人都认为他是个好孩子。他身高5英尺7英寸,体重120磅21,虽然个头有点矮,却是足球队的主力守门员。他的学习成绩也很好,待人谦和有礼,深受同学们的喜爱,并在同学们的推选下成为“未来最佳成就奖”得主。但没人知道在他和善的面具之下竟然有另一张面孔,他是个妄想型精神分裂症患者,吸食大麻和迷幻药以后情况更糟。
高中毕业后,他忽然堕落,让所有人都感到不可思议。精神分裂症常常被人误解,其实只是精神疾病中最常见的一种,而妄想型精神分裂症只是精神分裂症的一个分支。其实,妄想型精神分裂症本身并不一定引发暴力倾向,大多数普通人都多少有些这方面的倾向,只是轻重程度不同,而且大部分患者不会伤人。60年代末期,北加州有一批高中毕业的年轻人想要找回“迷失的自我”,马林的转变和这些孩子很相似。他毕业后进入大学学习,但学习成绩不佳,有一阵子他和许多人一样挂起念珠,留着披肩长发当了嬉皮士。再后来他发现自己无法找到女友而剪掉了长发,开始以西装革履的生意人形象出现,但这种改变并没有改善他的生活,后来他便进入一家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医生发现他性格温和,似乎不会对其他人造成威胁,便让他回家了。回到家里之后,他发现自己已经是个大龄青年,于是做出一些在街上或舞会上向女孩子求婚之类的荒唐举动,当然都被拒绝了。这一系列挫折让他很沮丧,进而认为自己是个同性恋者,便跑到旧金山同性恋者的聚集地去,开始当街向男人求爱,但仍然一再被拒绝。有一天他跑到一间教堂里大吼大叫,说基督待人不公。后来他又忽然想当牧师,但最终未能如愿。之后,他忽然冲到一家体育馆学拳击,教练看他身材矮小,便婉拒了他的要求。
最后他只好参军入伍,但由于他的父亲也是军人,因此除了陆战队以外,其他各军种都把他给刷了下来。陆战队先让他接受基本训练,但后来又发现他进入过精神病院而不让他做勤务,最后还撤了他的职。从军队出来后,他和一名同样患有精神病的老妇人住过一段时间,这时候他迷上了东方宗教及东方的神秘主义,于是跑到夏威夷“朝圣”,但毫无成果,后来还去过中国。
那时候他已经25岁,没有朋友,没有工作,完全被社会抛弃,可以说一无所有,只能偶尔打打零工,但工作时间从未超过一个月,因此一直靠双亲接济。与此同时,他的妄想型精神分裂症的病情更加严重了。
精神分裂症患者会把从各处得来的信息在心中综合起来,但最后分析得出的结论却让他们更加迷惑,因为他们无法把握事情的真正意义。比如,马林读到过加州大地震及地震预测的文章,于是认为加州可能将要发生强烈地震,这让他困惑不已,最终他给自己的解释是越战中美军大量伤亡导致了地震,而这个世界即将因此毁灭,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他需要用别人的鲜血来献祭。1972年2月,美军在越南战场上遭遇大败,马林更加确信加州即将地震,并有沉没于太平洋的危险,因此他需要用更多人的鲜血来献祭才能避免。在后来的采访中他告诉我们,父亲利用心电感应来给他下达杀人的命令。
我们在研究中发现“无组织罪犯”在作案前通常都有反社会的行为,而且是不由自主地产生这种想法,马林的行为也符合这一模式。他无法把自己正确地融入这个社会,无论是工作还是情感,都无人接受他。但这个时候他还没有实施过强奸、抢劫、偷窃或纵火的罪行,也没有触犯过法律,他因为没有犯罪记录,因此可以合法地购买枪支,但此后,他就开始了犯罪之旅。
马林的案子让警方大惑不解,这些杀人案件似乎毫无关联。首先,凶器不一样,目击者对凶手的描述也不相同,受害人的年纪、性别、致死原因和其他特征似乎也有很大差异;其次,当时肯珀也在这个地方疯狂作案,这让警方疲于奔命,无法专心地侦破此案。
马林第一次杀害的是一个55岁的男人,当时这个流浪汉正在高速公路上闲逛,马林看到对方后就故意放慢了车速并接近对方,这个老汉果然要求搭个便车。马林让对方坐在前座,然后从后座拿了一根棒球棒,不由分说就把对方敲死了,并把他的尸体拖到高速公路附近的一片草丛里。第二天,尸体被人发现,警方开始侦办此案。
两周后,马林又感觉到了父亲的杀人命令,为了净化这个世界,为了阻止地震的发生,他开始寻找下一个受害人。这次仍然是在高速公路上找了一个搭便车的人,但这次是个女子,凶器也换成了刀,他在开车的同时把刀插入了她的胸膛。等她死后,马林把尸体拖到了草丛里,先是剥光了她的衣服,然后把她的双腿捆绑在一起,接着就开始开膛破肚,以检查对方是否受到了“污染”。他把死者的内脏都掏出来检查了一遍,然后把内脏挂到了附近的树上,这次直到几个月以后尸体才被发现,那时候已经只剩下头颅了。两个案子有很大的差别,因此警方开始并没有把它们联系在一起。
马林是一个“无组织罪犯”,我在前文说过这种凶手不会开自己的车作案,但马林是少数的例外。这也证明我们的心理侧写只能成为艺术,而无法成为科学,我在学校教书的时候就对学员说在检查命案现场时,必须按照我所提供给他们的对照表核查,这样就容易评估及判断了。就本案而言,除了交通工具不符合“无组织罪犯”的特征之外,其他很多特征都符合,比如随机挑选受害人,没有预谋,没有刻意藏尸,无理性地开膛破肚等。虽然第二个被害人的尸体在几个月后才被发现,但这事纯属运气,并不是凶手策划的结果。
马林告诉我们,第二次作案四天后,马林对父亲指令的正确性产生怀疑,于是到离圣克鲁斯15英里远的一座教堂内找一个天主教教士忏悔,他坐在忏悔室里,因此教士无法看到他的样子。他向对方说了自己对父亲指令的疑惑,对方问他:“赫伯特,你读过《圣经》吗?”
“读过。”
“《圣经》里是不是说要遵守父母的训令?”
“是的。”
“我认为这很重要,我甘愿成为阁下的祭礼。”
马林马上踹门而入,连敲带刺,将对方杀死,然后夺门而出。
一位教堂执事目睹了惨案的发生,立刻跑出去求救,等警方到来的时候马林已经无影无踪,执事把马林的特征都告诉了警方。也许是眼力不好,这名执事把马林说成了高瘦体形的男子,因此反而误导了警方的调查。
我后来采访了马林,并研究他的人生在哪里出了差错,最后逐渐把注意力集中到了他的高中时代。有一次,足球队有个队友诱惑他吸食了一些大麻,这是他第一次吸大麻。后来他的精神状况不佳,就逐渐戒掉了大麻,但他从此非常仇恨那个害他染上毒瘾的队友。
1973年1月初,他到圣克鲁斯郊外的一处住宅来找那个队友,却发现那里住的是一个妇人。这个妇人的丈夫因为涉嫌贩毒被通缉,现在正在外地躲藏,妇人和他交谈了几句,告诉他那个队友住在这条路的尽头。他后来告诉我们,这个妇人坚持愿意将自己和孩子作为“祭礼”,就像那名教士一样。因此,他枪杀了一家人,然后到了队友的家里。
这名从前的队友、如今的毒贩邀请他进屋。马林也不客气,一进屋就责问对方为何把自己带坏,对方的回答让他很不满意,于是他开枪射击,对方挣扎到浴室外气绝身亡。那人的妻子当时正在浴室冲凉,他听到声音后要对方开门,等了一会儿没听到回答就破门而入,连她一块儿杀了。警方到现场勘查后认为这可能是毒贩黑吃黑,没有把这起案子和前两起案子联系在一起。
一个月后,马林在一片红树林区发现了四个十几岁的男孩,便走过去问他们在干什么。对方说是在露营,他马上说这块地是自己的,不容他们污染,并要他们立刻离开。但这几个男孩不买他的账,说法律规定此处可以露营,反叫马林滚开,几个男孩还从帐篷里拿出一把点22口径的来复枪示威。马林见状不敢再逞强,临走时说明天还会来看他们走了没有。果然,第二天马林又来了,并把这四个男孩全部枪杀,尸体在一周后才被人发现。
后来,他再次感应到父亲的命令,这时候他正开着一辆装满柴火的厢型车,他忽然看到路边有个西班牙裔男子在花园里浇花,他立刻把车转过来开到花园旁边,举起来复枪就射击。死者的邻居目睹了惨案的过程,赶紧打电话报警,警方从邻居口中得知了他的车牌号,立刻报告给附近的警察。几分钟后,马林被一位巡警拦了下来。他被捕的时候十分配合,毫不反抗,来复枪就在身边他也没有打算反击,警方在他车厢内又找到了那把取走前队友性命的手枪。
我在狱里采访他时发现他非常温和,彬彬有礼,而且长相英俊,但沟通能力很差。我每提出一个问题他都会说:“先生!我可以回房间了吗?”后来他告诉我之所以犯下这么多罪行,都是为了拯救地球。可以看出他患有严重的精神问题,应该留在精神病院治疗,而不应该被放出来。
那么,“有组织罪犯”和“无组织罪犯”谁更危险呢?哪种罪犯更多呢?这个问题不好回答,根据我们的研究和推理,大概三分之二的凶手属于前者,三分之一的凶手属于后者。
我认为,“无组织罪犯”从小时候到成年一直比较疯狂,他们会在被捕之前持续作案。我们对凶手的了解其实还很少,但他们就生活在我们中间,不会因为社会环境的改变而消失。此外,我推测“有组织罪犯”的比例会进一步上升,我们的社会在进步,同时武器也越来越容易获得,武器的杀伤力也越来越大,因而犯罪的破坏性也越来越大,而随着社会问题的滋生,各种关于强奸、凶杀的幻想也会越来越多。
